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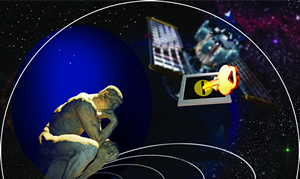
历史上,但凡一个国家的崛起均需要有综合实力的支撑,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也不例外。虽然人们对实力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除了一般接受的GDP总量、工业规模以及军事能力等传统指标外,政策制定者的战略眼光与本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质量日显重要。2011年8月15日,中国资深外交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唐家璇在题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论任务》一文中指出,“在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活跃和最重大变化的时期,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我们从思想理念上保驾护航。这项理论任务的完成需要我国大力发展智库。”毫无疑问,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参与国际事务空前的活跃,中国政府迫切需要具有战略眼光与处理危机能力的国家栋才,把握未来国际风云变幻中的中国外交走向。
“智库”通常也被称为“思想库”(Brain Trust或Think Tank),它是由多领域、跨学科的专家组成、为决策者在处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为目的的公共研究机构。
在现代社会中,智库积极协助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并能够有效改善公共政策。近年来,由于“软实力”理论广为流行,各国学界及政界普遍认为,智库在推动国家利益以及传播其“文化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历史上具有全球影响的英国和美国,便是通过有效使用智库为其内外政策服务的典型国家。
智库出现并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确立于“冷战”期间的英、美等西方国家。当时的一些学者以及某些退出公职的政府官员担负起为政府咨询的职责。例如,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A.Toynbee)1941年曾对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说:“我们是受雇于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为外交部提出的一切现实问题提供背景材料乃为我们的工作”。通常这一群体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而且多有实际工作经验。在英国第一代国际问题学者中,齐默恩、诺尔·贝克、怀特、卡尔、汤因比等或在本国外交部门或在国际组织有过参政、议政的经历。
故有学者认为,智库是“将其理念或研究结果让某一政治集团或权力中心接受;或改变他们对某一具体事态的立场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在这方面,美国知识分子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有参政、议政的传统。大学时期的美国学生就被告知“读书不仅是为了学位,更应该努力去获得知识,进入政府部门而担任公职则是为国家服务,以便使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中占有一个合法及适当的地位。”
一战后,英国意在设法保住其全球范围的既得利益,而美国则踌躇满志地审视他新获得的国际地位与影响。为此,两国在国际关系教育与智库建设方面表现得积极而有序。自1919年始,英国威尔士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美国乔治敦大学的外交学院(Georget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佛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相继建立了国际关系学科,以研究国际问题为主导。1924年英国成立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美国1927年建立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皆为世界上最早、最具影响的智库。
智库是以智力为生产力的一种特殊的群体,并通过这一生产力来为社会创造效益。就其功能而言,智库“通过对客观问题以及客观现象的研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预判,并得出尽可能客观、准确的结论,为决策者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回顾历史,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出现在英、美绝非偶然。当一战陷入僵持之际,英国学者在1916年编写并出版的《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即从外交史、战争之起源、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法、国际体系演变的视角论述了国际问题。其中有些核心问题——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依存论、民主和平论——60年后再次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热门话题。而此时准备卷入欧洲战争的美国更需要了解国际事务的人才,当时在乔治敦大学任教的学者沃什(Edmund A. Walsh)告诫说,为了避免未来“美国外交上的失利可能导致的国家灾难”,华盛顿政府应该即刻建设培养外交人才的专门学校。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英、美的知识群体率先推动了本国的国际关系教育,并同时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建设。
虽然一战后的英、美两国在战略上尚未形成同盟,但在政治、文化、特别是教育理念上却有着悠久的合作与相似之处。这不仅是由于此时的美国院校仍然部分地沿袭英国传统的教育制度,更重要的是两国对国际事务有着较为接近的看法。
在社会文化层面,研究公共政策的可行性植根于安格鲁·撒克逊的政治传统中。对此,两国强调国际问题研究需要以人文及社会科学结合的广博基础和专业知识的训练。英、美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十分重视教学内容中的人文、社会学科训练的必要性。在英国,国际关系学科强调外交史(即今天范围扩大了的国际关系史)、国际法与政治哲学思辨能力的系统学习,而当时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领域也是集中在这些较为成熟的传统学科。这一现象同样存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教育中。
英、美两国的国际关系教育体系的成型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创与发展时期(1919年—1939年)、美国主导时期(1945年—1970年)、“冷战”结束后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再思考时期(1990年—今)。尽管每个时期均有特色,但是,对师资的质量与要求则不会因某人的研究兴趣而发生“结构性断层”现象。此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总会出现一些献身教学、探索学科研究的领军人物。
二战后美国在国际关系训练中曾一度走向抽象的理论训练,原因是它忽视了人文素养与历史思维的培养。对此,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70年代,英、美等国的国际问题学者就此提出了批评及必要的“纠正”。今天,虽然在这些国家仍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研究机构急功近利地去迎合就业的需求、而非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或忽视从战略高度去思考理解复杂的国际问题,但在多数有着深厚人文传统的高等学府仍然保留着或至少部分地保留着外交史、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相关理论并重的传统。
建设智库无疑要求独立的思考,但同时它又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既需要教育机构发挥主导作用,也离不开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及支持。为此,智库的研究项目往往涉及到诸领域,因而需要跨领域的专家协作。
美、英智库的建设经验不仅来自其灵活的教学体制、多元的文化环境,以及注重经验的传统,其知识群体的积极参与和他们不断拓展国际话语权的努力更是不可忽视的考量。英国国际关系史学家威廉斯(Andrew Williams)在分析英、美知识群体建设智库的态度时写道:“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共同向往,英美知识精英们在逐步建立起一个包含社会、经济、思想等领域的国际体系的同时,并开始创建一个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理念的跨国资本阶级……他们的智库表现出来的使命证明,英、美知识群体在巩固其全球范围的经济、政治支配权的同时,正努力营造思想上的‘霸权’地位。”
显然,从中国传统的道德层面分析,这些英美智囊不能被称为真正的谋士,因为他们实质是以“谋国”为己任。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追求的是在全球范围的支配地位,他们故以全球化为旗帜,以思想趋同为理论来推行其文化的普世性。其结果是,仅以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为例,当今基本上仍然深受英美学者及其理论的影响。这种“言必之英美”的局面实为国际事务中的“思想霸权”。换言之,那些以推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英美知识群体,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为以追求支配世界为己任,但是,他们确以谋“天下”为目的,为其政府建言献策、修订理论、拓展影响、树立排他性的话语权。由此,他们对新兴国家的崛起,特别是对那些呼吁改变现存世界秩序中不合理规则的政府,十分关注甚至视为潜在的威胁。
作为公民社会的产物,智库不仅具有一般学术团体或社会组织的作用,而且需要表现出极大的承载力和创造力。具体地讲,智库应该在政府与公众之间予以沟通;分类与评估现实政策中出现的问题;以独立的声音为政策制定建言献策或提供建设性的信息。
在现实政策与国际战略性问题上,中国智库常常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很难让其拿出有效的“中国方案”。在中国硬实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日益缩小之际,软实力的建设却日渐相对滞后。
今天,中国社会对智库的认识尚在探索阶段。除了国家重点支持的智库外,来自高等院校的智库带有明显的问题。近年来举行的智库建设研讨中,列举的问题很多至今仍未提上议程,更难谈及解决。否则,唐家璇也不会在2011年重提智库建设,并指出“中国智库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参与程度还相当有限,更缺乏像英美拥有的那样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智库”。
目前国内“智库型”研究机构已多达2000余家;然而,被世界认可的只有74所。与世界排行前四位的美、英、德、法(1770、283、186、165)相比之下,中国智库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方面尚未达到与国际同行比肩的地步。
实际上,中国政府对智库的支持与关注是不言而喻的。财政上的支持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文化层面,中国人更具有古老的睿智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早在一百年前,美国传教士兼学者丁韪良(W. A. P. Martin)曾指出,中国人在两千年前,就在使用着近代欧洲国家才开始流行的理念、法律和惯例。这些“事实”折射出中国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一切条件。
说到智库的建设,拥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不乏睿智之辈、也不缺少历史经验。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承认失误的勇气、相互合作的气魄,以及长期发展的眼光和能力。建设智库绝不能重蹈几年前中国大学合并之风,其恶果之一就是至今许多高校的图书馆之规模或现状往往超过其藏书数量与质量。
同时,更要杜绝急功近利的心态。诚如基辛格对中国学者王莉丽所言,“作为智库,并非急于影响某一届领导人或其具体政策的某一(些)细节。智库的最大功能与影响力体现在给下届政府培养人才。”基辛格的这一解释是一贯的。早在60年前,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创建欧洲秩序》(A World Restored)中写道,政治家的经验与视野不能移植只能培养,但这需要时间。也许今天的智库能够起到这一“催化”作用。但关键取决于智库的质量与管理。特别是论及国家发展战略、涉及传统与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议题必须持以严格、甚至苛求的态度审视之。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取决其规模、行政级别、也不完全是公共关系,而是其研究成果的质量。眼下应该是把中国现有的庞大数量的智库加以整顿、优化的时刻了。如果说中国能够在相对贫穷的50年代创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哈军工的话,那么,作为当今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中国,就没有理由不能建成研究国际问题、心系国家安全的世界一流的智库。
随着中国日渐融入全球化中、并处在广泛海外利益的背景下,中国智库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在国际上有话语权,以建立自己的公信力。这就必然需要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协助政府或企业作出积极、务实的对策。在解决国家间纠纷、或磋商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全球和地区安全国际热点、焦点问题时,多提出些“中国方案”。
(作者为国际关系博士,供职于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